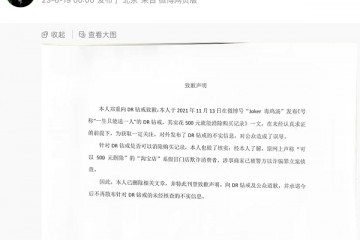笛卡尔认为,人类之外的动物不过是没有一点内在世界的“野兽机器”。在他看来,生理调节的基本过程与精神或意识基本上没有关系。而在苏塞克斯大学认知与计算神经科学教授、《意识神经科学》(牛津大学出版社)主编Anil K Seth看来,我们对意识自我的体验可能取决于以稳定自身混乱的生理与动物性的血液和内脏为目的的预测感知。我们是有意识的自我,尽管我们同样也是野兽机器——自我维持且渴望自身存续的血肉之躯。本文英文版刊于aeon.co,原标题为《真正的问题》(The real problem)。
理解意识的最佳方法是什么?几个世纪以来,哲学界一直在激烈地争论,宇宙是否能够按照勒内·笛卡尔的理论被划分为“心灵实体”和“物质实体”。然而,现代神经科学的兴起发展了一种更为实际的方法——一种以哲学理论为指导,但不依赖哲学研究寻找答案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不必通过解释意识存在的根本原因来揭示其物质基础,而应当在主观而现象化的意识与客观而可量化的物质之间架起阐释性的联结。
我在布莱顿苏塞克斯大学的萨克勒意识科学中心的工作时,就试图与认知科学家、神经科学家、精神科医生、脑成像专家、VR专家和数学家以及哲学家合作做到这一点。我们对意识获得了令人兴奋的新见解——这些见解有别于医学界的观点,却相应地带来了新的智力与伦理挑战。在我个人的研究中,一个新的图景也正在形成:意识体验可以被看作是深深地根植于大脑和身体共同工作来维护生理整体性——维持生命——的方式中。在此语境下,我们是有意识的“野兽机器”,我将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让我们从大卫·查尔默斯的观点入手,他提出区分“简单问题”和“复杂问题”,这种观点承自笛卡尔,有相当的影响力。“简单问题”是理解大脑(和身体)是如何产生感知、认知、学习和行为的,“复杂问题”则是理解为何以及如何将这些与意识联系起来:为什么我们有别于那些没有一点内在世界的机器人或哲学僵尸?人们常常认为,解决简单问题(不管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并无益于我们解决复杂问题,这种想法使意识的脑机制研究毫无进展。
但还有一个选项——我想将它称之为“真正的问题”:如何基于生物机制解释意识的各种属性;不试图假装意识不存在(简单问题),也不急于直接解释意识的存在(复杂问题)。(熟悉“神经现象学”的人会发现这种表达有一些似曾相识,但正如接下来我将阐释的,它们也有一些不同之处。)
这种方法在历史上已经有所应用,例如被用于生命研究方面。曾经,生化学家怀疑生物机制能否解释生命的本质。如今,虽然我们的理解仍未完整,但这种最初的神秘感已经基本消失——生物学家熟练地从根本机制上解释生物系统的各种特性:新陈代谢、内稳态、繁殖等等。此处一个重要的经验是,生命不止是个单一事物,它有许多有待分离的层面。
同样地,解决意识的真正问题在于区分意识的不同层面,并将它们的现象学性质(对意识体验的第一人称主观描述)映射到潜在的生物机制(第三人称客观描述)上。一个不错的讨论起点是区分意识水平、意识内容和意识自我。意识的水平与是否完全清醒有关,即,与处于深度睡眠(或全身麻醉)状态和有着清醒觉知之间的区别有关。意识的内容是当有意识时,你意识体验中的东西——构成你内在世界的景象、声音、气味、情感、思想和信念。而这些意识内容,就是“你”之所以成为“你”的具体体验。这构成了你的意识自我,可能是我们与意识最紧密相关的部分。
我们能拥有有意识的基本脑机制是什么?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意识水平并不等同于觉醒程度。当你做梦时,即使睡着了,也有意识体验。在一些异常情况下,比如植物人状态(有时被称为“醒着的无觉知”),人经历入睡和醒来的循环,但仍然可以绝对没意识。
那么,与仅仅是“醒着”不同,是什么使我们有意识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神经元的数量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小脑(悬挂在大脑皮层后部的所谓“小大脑”)的神经元数量是整个脑其余部分的四倍,但它似乎很少参与意识水平的维持。这甚至无关神经活动的整体水平——你的大脑在深度睡眠时几乎和清醒时一样活跃。相反地,脑的不同部分如何以特定方式相互交流似乎与意识紧密相关。
米兰大学神经科学家马塞洛·马西米尼的一系列研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证据。在这些研究中,研究人员通过一种叫做经颅磁刺激(TMS)的技术使大脑受到短暂的能量脉冲刺激,并用EEG记录它的“回声”(即反射回的电信号)。在深度睡眠和全身麻醉中,这些电信号格外的简单,就像扔石头到静水中所产生的涟漪。但在清醒状态下,特有的信号广泛分布在皮层表面,消失后继而以复杂的模式重现。令人兴奋的是,我们现在能够最终靠计算这些电信号的可压缩性来量化其复杂程度,类似于用简单的算法将数字照片压缩成JPEG文件。能做到这一点意味着朝“意识测量仪”迈出第一步,既具有实用性,又推动了理论发展。
意识的复杂度测量已经被用来追踪睡眠和麻醉状态下意识水平的变化,还可以用来检查脑损伤后意识的稳定性,因为基于患者行为的诊断有时会产生误导。在萨克勒中心,我们正在努力提高这些测量方法的可行性,希望能基于自发的神经活动(大脑持续的信号)而非外部刺激来计算“大脑复杂性”。我们的期望是,能拥有测量意识、量化意识起伏的能力,这将改变我们的科学认识,就像18世纪第一个可靠温度计的出现改变了我们对热(作为平均分子动能)的物理认识。凯尔文勋爵这样解释道:“在物理科学中,研究任何主题的第一个基本步骤是找到数值计算的原理和测量与之相关的某种质量的切实可行的方法。”
但问题在于,对大脑复杂度来说,什么是“优质”的测量?这就涉及到关于意识的新理论。这些理论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杰拉尔德·埃德尔曼(我之前在圣地亚哥神经科学研究所时的导师)和朱利奥·托诺尼(现就职于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认为,意识体验在同时具有高信息量和高整合性上是绝无仅有的。
意识是信息性的,因为每一次经历都不同于你拥有过或曾经可能拥有的经历。就像此刻,我坐在桌前,向窗外望去,感到从未体验过当下这种咖啡杯、电脑和窗外的云的细节的组合——这种体验与同时呈现的所有其他感知、情感和想法结合起来,更加与众不同。每一次有意识的体验都涉及到不确定性的大幅度降低,而这在数学上就是我们所说“信息”的意义。
每一次意识体验都是作为一个统一的场景出现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意识是整合的。我们不只是脱离形状去体验颜色,也不只是脱离背景去体验物体。构成我此刻意识体验的不同元素,比如电脑和咖啡杯,比如巴赫的轻柔旋律和我对接下来要写什么的烦恼,似乎以一种深刻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作为单一的整体意识状态的每个方面而存在。因此我们大家可以得到结论,这种数学(算法)捕捉到了信息与整合的共存,且可以映射到这种新兴的对大脑复杂性的测量方法上。
这并非偶然,而是“真正问题”策略的应用:我们从主观经验的角度对意识进行描述,并将其映射到对大脑机制的客观描述。
一些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这些观点,以解决这一难题本身。托诺尼是其中先驱,他认为意识只是一种简单的综合信息。这是一种有趣而有力的观点,但代价是承认意识可以无处不在,无所不在——一种哲学观点,被称为泛心理学。其中涉及到的大量数学变换也代表着,在实践中,真正的复杂系统的综合信息变得不可能测量。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例子,说明了如果研究人员囿于复杂问题而不瞄准真正问题,很可能会减缓甚至阻滞实验进程。
当我们处于意识状态时,一定意识到了一些东西。大脑中的哪些机制决定了意识的内容?解决这一问题的常用方法是寻找所谓的“意识的神经相关物”(NCC)。上世纪90年代,弗朗西斯·克里克和克里斯托弗·科赫将NCC定义为“合作产生特定意识知觉的神经元事件和机制的最小集合”。这个定义在过去二十几年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直接指导了许多实验。我们大家可以比较有意识觉知和无意识觉知,并利用脑电信号和功能性磁共振来寻找大脑活动的差异。有很多方法能做到这一点。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双眼竞争任务(binocular rivalry):给每只眼睛分别呈现不同的图像,以便有意识的感知在两只眼睛间交替转换(而感觉输入保持不变)。另一种是掩蔽(masking),在掩蔽中,靶图像短暂闪现,一个无意义的图案紧随其后,靶图像是否被有意识地感知到取决于图像与掩蔽物之间的延迟。
类似的实验已经识别出大脑中与意识感知稳定相关的区域,不论这种感知是视觉的、听觉的还是其他感觉方式。一些最新的实验试图区分那些只是口头报告产生了意识知觉时激活的大脑区域(例如说:“我看到一张脸!”)和真正产生意识知觉时激活的大脑区域。然而,尽管这些实验有许多可取之处,它们仍然没有真正解决意识的“真正”问题。比如说皮层后侧“热区”在意识知觉过程中被稳定激活,也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该区域的活动与意识相关。为此,我们应该一个概括性的感知理论来描述大脑活动的背后机制,而不仅仅是指出它们产生于何处。
19世纪,德国的赫尔曼·冯·赫尔姆霍兹提出,大脑是一个预测机器,我们所看到、听到和感觉的不过是大脑对其感官输入的最优猜测。换言之,大脑囿于一个脑壳之中,能接收到的都是模糊、嘈杂的感官信号,而这些信号并不与外界的真实事物直接相关。因此,感知必定是一个推理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模糊的感觉信号与人们先前对世界的期望或信念相结合,形成大脑对这些感觉信号产生原因的最优假设——是咖啡杯、电脑和云触发了这些感觉。我们正真看到的是大脑对外界事物的“最优猜测”。
在实验室和日常生活中,都很容易找到预测感知的例子。比如当我们在一个雾蒙蒙的早晨出门,期待着会在公共汽车站遇见朋友,那我们很有一定的概率会真的发现她就在那儿——直到走近仔细观察发现其实是认错了人。我们也可以在无意义的嘈杂声中听到有意义的言语,如果我们事先以为我们会听到这些言语(倒放《通往天堂的阶梯Stairway to Heaven》,齐柏林飞艇著名歌曲,译者注),你甚至可能可以听到撒旦诗歌)。即使是最基本的感知元素,也会被编码在我们视觉系统中的无意识信念所塑造。我们的大脑已经进化到习惯性认为光来自上方,这又会影响我们在暗处中感知形状的方式。
经典的感知理论认为,大脑以自下而上或由外到内的方向处理感觉信息:感觉信号通过受体(例如视网膜上的视细胞)进入大脑,然后深入大脑,每阶段都涉及到愈加复杂和抽象的处理。在这种视野下,知觉的“重任”是由这些自下而上的连接完成的。而赫尔姆霍尔茨的观点颠覆了这个框架,他认为从外部世界流入大脑的信号只传递预测误差,即大脑所期望的和它所接收到的信息之间的差异,感知内容是由从大脑内部深处流向感觉表面的自上而下的感知预测所承载的。感知是一个通过不断更新大脑的预测,在大脑感觉系统多个层次的同时处理中将预测误差最小化的过程。在这种通常被称为“预测编码”或“预测处理”的观点中,感知事实上是一种可控幻觉——大脑的假设不断受到来自外部和身体感官信号的控制和调整。心理学家克里斯·弗里斯在《下定决心》(2007)中富有说服力地表示:“这是一种与现实相符的幻想。”。
带着这种感知理论,我们再回到意识本身。现在,我们不必问大脑的哪些区域与意识(或无意识)感知相关,而可以问:感知预测的哪几个方面与意识相关?许多实验表明,意识更多地依赖于感知预测,而不是预测误差。2001年,哈佛医学院的阿尔瓦罗·帕斯夸尔·利昂和文森特·沃尔什要求人们报告漂移点阵的运动方向(所谓的“随机点运动图”)。他们使用TMS特定地阻断整个视觉皮层的自上而下信号,发现即使自下而上的信号传输仍然是完整的,对运动的意识感知也无法产生。最近,我的实验室更详细地探索了意识感知的预测机制。在几项实验中(源于之前提到的“双眼竞争任务”的各种变形),我们发现人们有意识地看到了符合他们所期望的信息,而不是有悖于他们期望的信息。我们还发现,大脑在所谓的“阿尔法节律”(这是一种存在于约10赫兹的脑电信号中的振荡,在大脑的视觉区域尤为明显)中的特定相位应用其感知预测。这个发现非常令人兴奋,因为它使我们得以窥见大脑可能是如何实现类似的预测性感知的,并且,它还为一种众所周知但功能至今却仍未明确的大脑活动现象——阿尔法节律——提供了新线索。
预测加工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特殊形式的视觉体验,比如由于精神病或迷幻类药物所产生的幻觉。一种基本观点是,当大脑对传入的感觉信号关注过少时,就会产生幻觉,因此这种感知会异常地被大脑先前的期望所支配。不一样的幻觉,包括从线条、图案和纹理的简单几何视觉经验到充满人事物的丰富幻觉叙述,可以被解释为:大脑过于急切地在大脑皮层层次的不同层次上确认其预测。这项研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和前景,因为它揭示了精神疾病症状的背后机制,就像抗生素能直接解决产生感染的原因以治愈,而止痛药不能。
在我们内在世界许多独特的经历中,有一个是尤其特别的——那就是“作为你自己”。人们很容易想当然地将自我体验视为理所当然,因为它们似乎无时无刻不存在着,我们无时无刻不感觉到主观存在的连续性(当然,从全麻中醒来时除外)。但正如意识不单单是一个简单事物,有意识的自我也应当被理解为产生自大脑的复杂结构。
首先,存在一种身体的自我,是一种作为一个身体并且拥有一个特定身体的经验;也存在一种视角的自我,是从某种第一人称的角度来感知世界的经验;还有一种意志的自我,包括意图和行动的体验——做这做那的冲动,以及推动事情的发生。在更高的层次上,我们会遇到叙事和社会的自我。叙事的自我是“我”进入的地方,是一种即使时间推移也始终作为一个持续和独特的人的经验,构建于纷杂的自传体记忆。而社会的自我是自我体验的一个方面,它通过他人的感知和想法折射出来,由我们个人的独一无二的社会生长环境所塑造。
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区分这些不同维度的自我。我们作为一些看似没有区别的整体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行动,我们身体自我的经验与我们过去的记忆,以及我们意志和行为的经验天衣无缝地整合在一起。但内省可能是一个糟糕的向导。许多实验和神经心理学的案例研究都指向了另一个不同的观点,在这个语境中,大脑活跃地不断产生并积极协调这些不同方面的自我体验。
让我们以身体自我为例。在著名的“橡皮手错觉”实验中,你的真手被挡在视线之外,主试会要求你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只假手上,当主试用柔软的画笔同时抚摸你的真手和假手时,你可能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那只假手现在莫名其妙地成为了你身体的一部分。这揭示了我们关于“拥有”自己躯体体验的惊人灵活性,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大脑如何判定世界上哪些部分是它所属的身体,哪些又不是?
为了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大家可以求助于有相同过程的其他感知形式。大脑根据其先前的信念或期望以及可用的感觉数据做出“最优推测”,相关的感官数据包括特定于躯体的信号,以及视觉和触觉等经典感觉。这些躯体感觉包括本体感觉,它是身体空间形态的信号,以及内在感觉,它包括大量身体内部信息,如血压、胃张力、心跳等等。身体自我的体验依赖于对与躯体相关信号的预测,包括内脏感觉和本体感觉跨通道的感觉信号,以及其他常见感官跨通道的感觉信号。我们作为和拥有一具身体的体验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受控幻觉”。
我们实验室的研究也支持这个想法。在实验中,我们使用所谓的增强现实技术开发了一个新版本的“橡皮手错觉”,旨在检查内部感知信号对身体所有权的影响。参与者通过头戴式显示器观察周围环境,注意力集中在他们面前出现的虚拟手上。根据程序设定,这只虚拟的手会有节奏地闪烁温和的红色,闪烁的节奏可以与参与者的心跳节律保持一致,也可以不一致。我们观察到,当虚拟手与心跳同步脉动时,人们会体验到更大的身体所有权认同感,而这恰恰验证了我们的假设。其他的实验室发现类似的原则也适用于意识自我的其他方面。例如,当传入的感觉数据与行为的预测结果相匹配的情况下,我们会体验到主体性,而在精神分裂症等情况下,我们会体验到主体性的崩溃,这种崩溃可以回溯到预测过程中的异常。
循着这些发现,我们一路回到了笛卡尔的观点。我们“我猜(我自己)故我在。”/“我预测(我自己),所以我存在” 作为你(或我)的特定体验,不过是大脑对自我相关感觉信号产生原因的最优猜测。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反转。预测模型不仅能够找出产生感觉信号的原因,而且通过改变感觉数据以符合现有预测(有时称为“主动推断”)能使大脑能够控制或调节对应的感觉产生原因。当涉及到自我,尤其是其深度表征时,高效的调整可以说比准确的感知更为重要。只要我们的心跳、血压和其他生理指标保持在安全范围内,即使缺乏详细的感知表征,可能也无关紧要。这可能与“作为一具躯体而存在”的特性有关,与对世界上其他客体的体验或将躯体作为客体的体验相对而言,这种体验具有独特性。
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笛卡尔。在将身心二分的过程中,他认为人类之外的动物不过是没有一点内在世界的“野兽机器”。在他看来,生理调节的基本过程与精神或意识基本上没有关系。恰恰相反,在我看来,我们对意识自我的体验可能取决于以稳定自身混乱的生理与动物性的血液和内脏为目的的预测感知。我们是有意识的自我,尽管我们同样也是野兽机器——自我维持且渴望自身存续的血肉之躯。